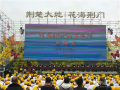奶奶,您在哪里?
李放鳴
不知歷史上的哪一個年代,“嘩!嘩!”的連天大雨下了個天地間日夜不斷線,沉沉的烏云和雨霧,彌漫籠罩著山峰、地坡和田野,久久不能散去——在這連綿起伏、橫亙在攸醴兩縣邊界的桐嶺大山邊,發生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洪災!山洪從這氣勢高高的山峰上,拍打著它兩岸的懸崖峭壁,飛濺著白白的浪花,象千里躍進的戰馬,吼著汽浪,瀉下山來。瀉得那野生在山壁上的樹木根兒露露;瀉得那大大小小的山石,“咔咔嚓嚓”地滾下山坡。突然,在這“嘩嘩”奔瀑的洪水聲中,夾著“轟!轟!轟!”的幾聲巨響,震的山搖地動,震聲在這深深的山谷里久久回響。忽地兩個巨大的石頭,伴隨著奔瀑的洪水,一前一后地隨即進入了這座高峰下的山沖,又繼續地滾了下去。滾著,滾著,滾到了山沖的中腰,不知什么緣故,竟笨立地“窩”在這山沖低洼的江床里,一動也不動了。人們都說,正是因為這里有兩只大蛒蛄精,特地叫“上帝”為它搬來,作“家”住的。從此,這兩只“蛒蛄精”各居一個“家”,屹立在這山沖的正中,度年過月。因此,人們特地為這個無名山沖,起了一個有“根據”的名字——“蛒蛄沖”。
“蛒蛄沖”是個荒涼空曠的偏僻山沖,只有一條崎嶇的山路,長年累月,也難得見到幾個過經的人。綢密的山林,竟相生長在這山沖的上上下下,開花落葉,周而復始;林間,百鳥爭鳴,展翅飛翔,搜山巡林。山下各種雜草,四處叢生;山澗,“明月松間照,清泉石上流”;山上山下,野獸眾多,弱肉強食,虎豹揚威控大沖。盡管野獸眾多,但難見幾名獵手來捕殺它們。千百萬年來,這樹木封山、雜草遍地的山沖,只不過是一個野生動、植的世界,無人開發,更無人住家……
后來,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進程,到清末民國,人口有了發展,苦難的勞動人民,迫于生計,開始到這個“虎嘯狼嚎”、“天高皇帝遠”、尚無人問津、山地無主的地方,開始開荒栽樹、造田造土。在鐵與火的宣戰下,它漸漸地換了模樣,山沖中出現了一層層梯田,一塊塊新土,一片片油茶林。于是,它變成了農人希望的地方——春天,山沖中一片片小麥,被春風吹得垂頭鉤腦地成熟著;夏天,被陽光雨露哺育成長的稻子,由青轉黃地結果著;秋天,滿坡的油茶,“笑盈盈”地供人采摘;十月間的紅薯挖不盡,季季蘭草花開,鳥兒“啾啾”鬧著山,清涼的溪水涓涓長流……這里一時間,又似乎成了一塊“世外桃源”。
時間到了1968年的秋天,我們祖居的爐下上下兩垅,人口由解放初期的10多戶、40多人,迅速發展到30多戶,130多人,并且全部“窩”在家里搞“大集體”。過度開發、消耗、榨取大自然資源。“蛒蛄沖”和下面的矮山一樣,山林、地柴也被砍光了,路旁、坡中的“草皮”被鋤凈了,虎豹早已絕跡。被“文革”鼓燥了三年的人們,決定在蛒蛄沖辦一個什么場。由于有大量的勞力,砍的砍竹子,斫的斫冬茅,僅用數天功夫,就選擇在沙子坡與同老湖兩沖交界的山咀下的一塊小坪地,搭起了一間占地約30—40平方米的、由竹子當墻、冬茅蓋頂的簡易住房。于是,我奶奶——人稱“八嫂婆婆”,便成為這山沖中“三皇五帝”到如今,第一位,也是唯一的一位居民。

當年住房之地已是一片荒草
當年,我奶奶已50多歲,身體有病,又單身一人,為什么會能享受這一空前的、如此“厚愛”呢?這得從我奶奶王回英的悲慘身世說起。
我奶奶王回英于1910年10月出生在坪陽廟鄉坪泉村榴槐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,其弟叫王克昌。我奶奶王回英成年后,不知什么時候,嫁入爐下的李宗生,她的丈夫于1956年病逝。那時,由于我祖父李天生與第三個妻子已離婚數年,他們又同住在近在尺咫的爐下灣里,雙方都無對象,兩人年齡相仿,相貌、性格合意,就開始了“來往”,成為沒有辦領結婚證而同居的“事實夫妻”。在我的記憶里,他們能互相尊敬、互相體貼、有事商量,一團和氣,從沒斗嘴,從沒扯皮,過了“風雨同舟、患難與共”的四五年恩愛生活。可惜,好景不長,祖父在1960年春,被惡人打死了,奶奶重又過著單身生活,住在我家下蘇屋那廂的幾間小房里。至1967年秋,我四弟出生,全家和奶奶共有7個人,卻只有一個僅9分底分,不能算作全勞力的父親一個勞力,在那靠勞動工分吃飯的大集體年代,我家無法吃上最基本的用糧水平,年年欠著隊里一大把賬。因此,隊里根據這種困難情況,特別將一頭老黃牛分配給奶奶放養。這頭名叫黑古的公牛,平時顯得老實巴交,性情溫和,誰都可以接近它、撫摸它。可是,有一天下午,我奶奶在沙樹嶺下一丘名叫“七擔” 的稻田里去放養這頭黑牛,它一反平日的溫順,卻把放養它的恩人——我的奶奶,突然當成一個大仇敵似的看待,居然蹬著兩只紅紅的眼睛,趕著我奶奶狠斗,我奶奶遇此“突然襲擊”,一時毫無防備,被它抵斗在田壁上。這時,我奶奶只好一邊大聲呼救,一邊用右手緊緊抵著它的鼻子往上扭來巧力制約它的兇斗。后來,在別人的幫助下,才將它驅走。但是,奶奶雖然脫離了險境,一條腿卻被它斗成了“瘸子”。鑒于這種情況,隊里為了維護我奶奶的人身安全,只好將養護這頭牛的事兒調給別人,而奶奶卻每年失去了放牛的60個工分,落得生活沒了門路。因此,隊里為解決奶奶的生計,就將奶奶安排到蛒蛄沖這間草竹結構的棚子中去“守廠”。于是,奶奶沒有任何拒絕,沒說半個“不”字,就在我們的幫助下,卷著極為簡單的鋪蓋和日常生活用品,在這極簡陋的“家”中居住下來。由于這里特別偏僻,周圍數里無一戶人家,連雞啼狗吠聲都聽不到,只有山中的鳥鳴和地下的蛙聲、蟲聲相聞。好在虎豹早已絕跡,不存在生命威脅;好在“文革”的大破“四舊”,在心頭散了神鬼的恐懼;好在沖中的樹柴砍完了,才無從前的那種陰森森的害怕感覺……于是,我奶奶就這樣命運無情地迫使她離開真正的人住的家,而獨身一人到山野的、遠離人群的、不是人住的深山,去孤楞楞地、擔驚受怕地“生存”。可是,奶奶卻能象楊柳那樣,無論插在江里、塘邊、田埂,它都能成活一般地靈活面對。于是,奶奶在草棚邊挖了許多土,適時種了四季都有吃的零星蔬菜;在棚邊攔了一小池溪水洗衫洗菜;在涯下挖了一口小水井,以燒茶煮飯……能“適應”這特殊的“新家”,幾個月沒有回來。那天,我和定英姐特地到蛒蛄沖去看望她,她對我們顯得很慈愛,很親切,并掏出一只鎖匙,叫我倆到老屋地樓上為她找一些東西帶去。于是,我倆按照奶奶的吩咐,去“地樓”為奶奶找東西。可是,雖僅隔數月,當我倆打開“地樓”門鎖進入,短暫數分鐘的時間,由于“地樓”下常年關著隊里的牛,滿屋牛糞臭氣往上彌漫,“地樓”幾月未開門流通空氣,一股令人窒息的霉臭氣向我倆襲來,一下子滿身隨之生上了豆粒般大的,又腫又庠的紅胗。
秋去冬來,蛇類要入洞冬眠了。可是,有一條顏色像綠枝綠葉一樣色彩的青竹蛇,靜悄悄地偷偷爬到奶奶住的草棚里,進而又爬到床的蚊帳上,后來,縮在床下,奶奶一時沒有發覺與及時防避。于是,有一天下午,奶奶不幸被它咬上了。而且,青竹蛇是一種與眼鏡蛇、五步蛇、百節蛇一樣劇毒的惡蛇,它的毒液迅速竄入了奶奶身上的血管,使奶奶光潔的腳腿上頓時生起了一個個圓鼓、通亮、透明的磷片樣的大氣泡,奶奶呼吸短促,面臨著生命危險。后來,奇生外公及時找到一副好蛇藥,才在死亡線上挽救了奶奶的生命。

奶奶就曾住在這遠處的高山下
從春的花開花落,到夏的酷暑難挨,到晚秋的涼風瀟瀟,到冬的風刀霜劍,奶奶忍著孤單,忍著寂寞,忍著辛酸,從1969—1970年在這個廠棚里繼續苦熬了兩年。
1971年上半年,奶奶得的嚴重的“崩病”(子宮癌),到了晚期,我們不得不將奶奶接回老家,讓她重新住在她與祖父原先住的那幾間小房里。沒有正常的食物營養,沒有一分錢的治療經費,就這樣“坐等待斃”地耐著劇痛,被癌癥苦苦折磨著,生命陷入了絕望。
大概是1971年的農歷5月中旬,恰逢禮拜天,我從攸縣二中回家。第二天,是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天,上午,大家看到奶奶快不行了,忙差我到雙雅沖里的姑母家拿“裝尸布”,我冒著火辣辣的太陽,來回跑了20多里崎嶇的山路,午后才回到家里。我親眼看到了易連英(四嫂伯母)等一大群人圍在奶奶身邊,奶奶就在她住的那間房里的床角又臨墻的一個高栮子的便桶上蹲著,大滴大滴的汗珠從她的額頭上掉下來,寸長的灰色的象腸子般的東西,一截截地慢慢從她身上丟到便桶里,看得出,她是多么多么的痛苦……不一會兒就斷氣了。就這樣,天底下一個多么可憐、多么值得同情的人,悲慘地離開了人間。
一個星期內,我父親和炎云叔叔一道,不知是怎么弄來一副棺材裝斂,買了許多肉和鱔魚(那時便宜)、黃瓜、辣椒等,將奶奶埋葬在“十字路”上面的一個山頭上。她在坪泉大隊的“娘家人”也趕來送葬。
奶奶遠去了,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:奶奶個子不高不矮,身材不胖不瘦,圓圓的臉盤,五官端正,并布局均勻,臉部輪廊線條舒緩,只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心地十分善良的女人。的確,她一生盡管無兒無女,坎坷多舛,但她從未做過任何傷害別人的壞事和惡事。她從不和別人爭辯什么,也沒有什么癖好。

奶奶用過的量米升子
奶奶的許多生活片斷,至今還記憶猶新:
夏天來了,她常在我家的下蘇屋對著廠下的門口,脫去上身的衫衣,搖著老葉蒲扇納涼;在廠下屋的階級下面,折著幾枝帶青葉的小樹枝,用秕谷壓在面上,點火燒著濃濃的青煙來驅蚊。冬天來了,我們在奶奶的小灶屋一塊烤火、算數、猜謎;我還清楚地記得珍如公在60年代里喜歡在烤火時,拖著長長的、半唱的嗓音念著報紙;1961年姑姑初嫁雙雅大隊的下江沖,細心的奶奶第一次就數清了從雙雅水庫進口處到其家里,要過十八座小木橋。
奶奶是仁慈和愛家的。小時候,她和祖父帶著我走過她的坪泉大隊榴槐沖娘家;1960年過“苦日子”的時候,隊干部半夜偷偷在我家“斗伙”,奶奶有兩次趁機留著難得的飯菜,偷偷送給睡夢中的我。祖父因所謂的“落后”,常遭到左傾干部黃某、吳某的批斗,奶奶每次都是硬著頭皮為他在他倆面前求情;祖父被吳某打殘后,是奶奶天天陪伴在祖父身邊,為他生火取暖、做飯、煎藥。最難忘的一件事是:大概在1961年或是1962年,有一次生產隊將一架原是我家(已入社)的橫田鐵耙,用后丟在我家忘記收回,在那極左年代,奶奶趁機冒險將這架鐵耙收藏在灶屋樓上,為我們留下了值得永遠珍藏、永遠紀念的祖父母共同的、唯一的遺物。

奶奶收藏的鐵耙
……
時間一晃,數10年過去了。清明節又到了,家鄉煙雨濛濛,山頭到處開遍了一叢叢美麗的映山紅,我和文明弟弟攜著幼小的孫女若靜,又一次地來到奶奶墳前祭拜。迎面處,高高的彤嶺大山上,厚厚的云霧遮沒了整個山峰;下邊就是奶奶當年住過“家”的“蛒蛄沖”,曾經的廠棚沒了蹤影,坪里長滿了齊腰高的雜草和冬茅,小水池不見了,小水井不見了,只有江中那兩座“蛤蟆石”還一動不動地“蹲”著,鳥聲、蟲聲依舊,山沖還是原來的模樣。奶奶,今天,我們特意來到了你過去住過的地方,淚水已模糊了我的眼睛,我們想您!您在哪里?您在哪里?您在哪里?我們在無窮無盡地深深呼喚您!呼喚您!!呼喚您……(李放鳴)
相關熱詞搜索: